熊芷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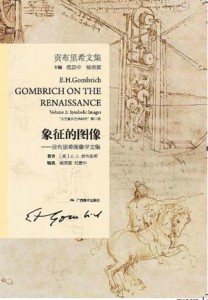 贡布里希在其著作《象征的图像中》,提出了关于图像及其意义的问题。他以一座立于伦敦市中心的厄罗斯(Eros)雕像为例,提示读者注意一个问题:即便存在着关于厄罗斯的一套完备神话故事体系,同时观看者可以借助作者本人对作品的解释,以及最初的设计方案作为参考,想要“复原”这座雕塑所传达的意义,也是极为困难的。事实上,对于图像同语言、意义的关系,自古以来便被广为讨论,人们无法修订、甚至设想一部图像对应其象征意义的权威辞典,而在文字语言领域我们却能够接受这样的辞典。图像与语言,以及以语言为主的人类意义体系之间,似乎存在着隔阂。普鲁斯特也曾颇为遗憾地说:“我们在一个世界里感受,在另一个世界里命名。”
贡布里希在其著作《象征的图像中》,提出了关于图像及其意义的问题。他以一座立于伦敦市中心的厄罗斯(Eros)雕像为例,提示读者注意一个问题:即便存在着关于厄罗斯的一套完备神话故事体系,同时观看者可以借助作者本人对作品的解释,以及最初的设计方案作为参考,想要“复原”这座雕塑所传达的意义,也是极为困难的。事实上,对于图像同语言、意义的关系,自古以来便被广为讨论,人们无法修订、甚至设想一部图像对应其象征意义的权威辞典,而在文字语言领域我们却能够接受这样的辞典。图像与语言,以及以语言为主的人类意义体系之间,似乎存在着隔阂。普鲁斯特也曾颇为遗憾地说:“我们在一个世界里感受,在另一个世界里命名。”
然而,这个隔阂却不意味着绝对的断层,否则,我们便不可能欣赏艺术作品,更无法对它们进行任何层面的解读了。从原始的象征符号,到先进的种种艺术作品,以及更具代表性的电影(作为一种运动的图像)的出现,无不暗示着我们,在图像中有一个“叙说”的空间,它不是单纯的“展示”,而具有深层次的表意功能。
当然,在这里使用的“叙说”一词,与日常中使用的意义和叙事学上的严格定义有些不同,只能笼统地以这个词概括它所涉及的象征、表意等问题。而同时,这种“不同”也恰恰是图像的迷人之处。在观看画作、图像时,许多人会将当时的感觉描述为“难以言表的”,而“无言”正是图像的特征。在言语终止处,图像往往意犹未尽,在“绘画者——观看者”的传递中,图像带来了远远超出色彩、大小、材质等属于它们的东西,而给人以情感上乃至于神秘的体验。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及其本原》中谈到了梵高的绘画,认为他的绘画直接展示了“存在”,也就是“本真”。在这里,图像的“作者”退隐了,建立了“观看者——图像——存在(真理)”这样一种关系,作者起的只是一种为存在建基的作用。在原始社会中,图像作者的名字、身份等等信息往往不为人知,图像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作者存在,作为一种原始符号承担起人和神之间桥梁的作用。即便今天我们不再如同原始信仰一样去谈论神,而用那个以自然为代表的真理、超越性存在取而代之,图像同样在产生着这样的作用。
“模仿论”在图像的历史上占据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为著名的论述来源于柏拉图的著作,他认为图像因为是对现实事物的模仿,而事物又来源于理念,所以图像、艺术作品“三倍远离”了现实。模仿论在后来的历史中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包含着消极和积极两种态度,但无论如何,“艺术模仿自然”都是这种理论的核心。模仿说成了晚近的“镜子说”的雏形,图像使人目睹了“自我”在自己面前呈现。在古埃及,人们将为死者绘制的雕像当做死者的提神,人因获得了在时间中长存的图像而获得了不朽。图像继承了人们对不朽的渴望和浮想,经由死亡,建立起了从人到神的连结。
模仿说在艺术和文学中均有其重要地位。但在谈论“模仿”时,我们恰恰不能把图像和语言混为一谈。作家写下“红色”一词,同画家画下一笔红色,在直觉上都会令人觉得非常不一样。对“颜色”的感觉事实上很难用文字去描述清楚,也就是说,对于自然界中的某个颜色,人们在语汇中是找不到严格对等的词的,即便有色谱存在,人们也已经习惯于用“红色”去指代各种各样被我们称为“红”的颜色,在这里深究下去仍然会遇到艰难的形而上学问题。但在画家的情景中却不一样,“他享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即造就自然。……处于世界难以名状的开端。”[1] 画家的红色无需进行指称,只需要被人们看见,就已经“是”它所是的东西。较之于文字的命名和叙事功能,图像在这里像是在进行“创造”和“展示”。
诚然,“展示”或许是图像和图像艺术最大的特征,它直接面对人的视觉,在感官的层面上,往往比经由理性思维处理的文字带来了更强烈的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代世界,图像的传播速度和效果要远远大于文字,在触动人心的层面上,它也常常带来瞬时性的剧烈作用。相比之下,文字著作则需要去阅读、思维和反思,因此,它的表达效果往往需要经由一段时间,并通常会得到一个较之于图像艺术来说更为冷静的思考结果。
语言特别是文字语言,最大特征是“可翻译性”,词典的存在意味着一门语言中的词语、句子可以被转化为“意思”,从而被翻译为另外一种语言。即便这样的翻译会因为文化差异等等原因而不能达到完全的精确,但基本意思的转化仍然是可以达成的。但在面对图像时,我们却几乎不可能达成这样的翻译,很难想象一副图像可以被“转译”为另一幅图像。布格罗绘画中的厄罗斯无法被转译为伦敦市中心的那座厄罗斯雕像,同样也不能被另一幅画中的厄罗斯所替代,即便这些作品的对象都是同一个神话人物,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完备的神话体系作为支撑,观看者对于其中的文化、艺术背景都有相当的知识,但两幅绘画仍然可以表现全然不同的东西,人们也可以对其作出截然相反的解读。
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表意,使得图像和绘画艺术远远不止步于在一个框定的空间里展示一定量的内容。这其中的象征,建立的是“人——图像——人”这样一种关系,自然,这之中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文化背景,才能令无声、沉默的视觉传达,在人的语言和前语言阶段中得到呈现。如雷吉斯·德布雷在《图像的生与死》中所说:
Symbolon,来自symballein,是聚会、合拢、接近的意思,最初指的是某种待客的信物,杯或碗破城两半,主客各执一半,传给自己的子女,期望有朝一日他们将两半对接起来,建立同样的信任关系。……象征标志乃是约定之物。[2]
由此可见,象征作用在传递的过程中,有一个“拆解——重建”的过程,观看者的眼睛接受了作为整体的图像,也接收到了其中的各种信息。但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有赖于观看者自身的许多主观因素,诸如文化、教育背景,观察的敏锐程度等等。在重组这些信息的时候,往往又会与自己身处的文化、地域特质糅合在一起,一座山的图像在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眼中或许会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东西。也正是因为象征的复杂,图像学全然不同于图像志的工作。
编纂图像志的人,往往会将一些图像的表意功能,通过符号化的整理,罗列出一些常见的意义。但即使是编纂者自己,也会强调这种归纳和罗列的片面性和不完全性,这更类似于兴趣上的收集,而不是严格的字典编纂。如果图像的表意仅仅被缩减为“符号”,那么它就被极大地狭义化了。
假如借助文字语言中的“叙述”概念来类比图像,那么也同样存在我们“阅读”图像的行为。在“阅读”某一图像的时候,我们并不像是阅读文字一样,首先去“识字”并“读懂”——或许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说自己“看不懂”一副图像——图像是直接呈现于眼前的。其次,叙事中最小故事的概念,包含了三个以上时间接续的事件和因果关系这两个要素,然而图像本身却不具备因果关系(即便它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一个故事性情景),人们去阅读图像,就是在这种无声的语言当中,将图像和自己脑海中的文化背景和种种线索加以重组,从而得出一个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人的“故事”。任何一次观看都是一次全新的创造,这或许就是“观图”的有趣之处。
[1] {法}雷吉斯·德布雷 黄迅余 黄建华译,《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页。
[2] {法}雷吉斯·德布雷 黄迅余 黄建华译,《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