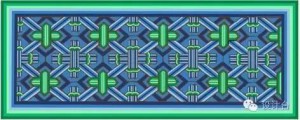邹其昌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以全新的视角,以当代现象学的诠释方式,探索了中国美学史写作的新途径。文章认为美学史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三个基本领域,即美的事件、美的思想和美的理论。美的事件主要是指美的形而下的生存样态或结构,包括日常生活的喜闻乐见之活动、生活方式、民族习俗等等,亦即物质文化领域为主体的活动,但有别于当下所谓的“审美文化”。美的思想是指与美学相关的思潮,如理学、玄学、禅宗等。美的理论是指美学自身建构的理论系统阐释或命题,如意境论等。就其三者的关系而言,美的理论是美学史研究的核心,而美的思想是美学理论产生的理论背景,美的事件则是美的理论和美的思想生长的最后根源,这也是当代世界美学研究的中心。在此,文章通过“诗文美学”、“书画美学”、“词曲美学”、“音乐美学”、“设计美学”等几个基本方面展示宋元美学的平淡境界追求。“平淡境界”大致以美的理论方式展开对宋辽金元美学问题的讨论。
关键词:中国美学史;宋元美学;生活世界;美的事件;美的理论;平淡境界
宋辽金元美学是中国传统美学高度繁荣发展时期,审美领域之广、审美风格之盛、审美流派之多、审美境界之高都属罕见。艺术美学领域的境界追求无比丰富。词学美学有豪放派、婉约派之别;诗学美学有“诗有别材,诗有别趣”之议;文论美学有“文以载道”、“文道两本”之趣;绘画美学有院体画、文人画、工匠画等不同流派,还有“北宋三家”“南宋四家”“元四家”等不同风格;音乐美学有“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多样发展的格局;建筑装饰美学有“五彩遍装”“碾玉装”“青绿叠晕稜间装”“解绿装”“丹粉刷饰”和“杂间装”等多种样式与风格。当然,宋辽金元美学的主体是由两宋美学来代表的,而两宋美学在对中华美学整体继承与多元探索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升,并提出了自己的时代审美追求。这一追求在多种境界并存的同时,突出平淡的境界。
一、诗文美学的平淡境界
在宋初诗文革新运动中,梅尧臣就提出了平淡理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这“平淡”主要源于以《诗经》中的《周南》气象。他在《依韵和晏相公》诗中说:“微生守贱贫,文字出肝胆。一为清颖行,物象颇所览。泊舟寒潭阴,野兴入秋扊。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未圆熟,……兹继《周南》篇,段桡宁及舰,试知不自量,感涕屡挥掺。”(《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6)平淡也不是平常,而要“深邃”、“正静”“博远”。他的《林和靖先生诗集序》说:“其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主乎静正,不主乎刺讥,然后知趣尚博远,寄适于诗尔。”(《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拾遗》)这里的“平淡”并不只是钟嵘“淡乎寡味”之“平淡”,而是指追求“中和平正”,平中见出情趣、淡而味长,“读之令人忘百事”的淡远深邃的审美境界。梅尧臣这里继承了儒家美学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这一传统内化为自己创作的基本理念,具体展示了儒学复兴思潮在文艺审美领域中的渗透维度,同时也预示着一个不同于汉唐崇高美学的宋代崭新的审美思潮的出现。欧阳修在《六一诗话》对梅尧臣的平淡作了总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1]这里,欧公所转述的“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作为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要求古文写得易知易明,但却要含有不尽的深意。苏轼进一步推进了平淡的内容,他说钟、王的书法“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韦应物、柳宗元的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2]也说陶渊明和柳宗元的诗“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3]在他看来,平淡是看起来淡,而实际上是浓,浓包含在淡的外表之下;看起来是近,而实际上是远,远内含在近的外表之中。这种内蕴着浓和远的平淡是要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4]把苏轼最后一段话用来比较唐代之美与宋人之美,可以说唐人之美是“气象峥嵘”,而宋人之美是“乃造平淡。”
朱熹曾探讨过平淡境界从梅尧臣到欧阳修到苏轼的演进过程,说梅诗一方面“闲暇萧散,犹有魏晋以前高风余韵”(《朱熹集》卷64),另方面说“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朱子语类》卷139)。说欧阳修诗“枯淡中有意思”(《朱子语类》卷140),说欧阳修文“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有好处,有不可及处”。谈欧文与苏文时,说:“欧文如宾主相见,平心定气,说好话相似。坡公文如说不办后,对人闹相似,都物恁地安详。”(《朱子语类》卷139)
朱熹也主张“平淡”,却以儒家的“中和”为根底,首先要“文字奇而稳方好”(《朱子语类》卷139)。所谓“奇”是讲究“诗字字要响”(《朱子语类》卷140)。所谓“稳”是要“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朱子语类》卷140)。这两个方面的效果,则是“如月影散落万川,定相不分,处处皆圆”(《朱子语类》卷139)。如何做到平淡之圆呢?朱熹提到要心灵的虚静:“若虚静而明,便识好物事。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心里闹,如何见得!”(《朱子语类》卷140)“教他里面东西南北玲珑透彻,虚明显敞,如此,方唤做虚静。”(《朱子语类》卷121)作为理学家,朱熹的平淡讲究来源之正和本性之真,他说:“夫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自有诗之初以及魏晋,作者非一,而其高处无不出此。”(《朱熹集》卷64)只有诚中形外,方有平淡,即“漱六艺之芳润以求真澹”。[5]作为理学家,在理之中寻出一个“趣”来,自然达到平淡。
二、书画美学的平淡境界
欧阳修还把平淡理论从诗推及到画,《画鉴》云:“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之。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尔,非精鉴者之事也。”[6]提出的仍是平淡的最要之点,淡泊之意和趣远之心。
宋人的平淡是一种胸怀。这一胸怀体现在书画里,就是苏舜钦提出的“人生一乐”的思想。欧阳修对此非常欣赏,并在《试笔》一文多处发挥:
苏子美尝曰:“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试笔·学书为乐》)
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于静坐中,自是一乐事。(《试笔·作字要熟》)
这种写字之乐在石苍舒那里体现为作书时展墨的“醉”,所谓“醉墨”,也就是写书法是为了达到自己心里的快乐,而不强求写得好不好。苏轼对此非常欣赏,同样多处发挥: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意逍遥游。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消百忧。(《石苍舒醉墨堂》)
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又贤于博奕也。(《题笔阵图》)
米芾对这种对等作书作画的思想,称为“戏墨”。戏,也就是“乐”和“玩”的意思,一种审美的非功利态度。其《书史》说:“何必识难字,辛苦笑杨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工拙。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7]这一作书作画的超功利态度,反过来也影响到文学方面,黄彻《潜溪诗话》自序:“平居无事,得以文章为娱,时阅古今诗集,以自遗适。”[8]陈俊卿在为该诗话作序也说:“时取古人诗卷,聊以自娱。因笔论其当否、且疏用事之隐晦者以备遗忘。”[9]用同一种审美态度打通书画诗文,成为宋人的一种普遍现象。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也。”(《苏轼文集·文与可画竹墨屏风赞》)书、画是诗之余,词,也是诗余,这是一种公论。把握“玩”是理解宋人艺术的一个关键。
这种乐、玩、戏,从一种不经意的平淡中出来,实际上是拒绝日常功利的“俗”,而追求文人趣味的“雅”。这种平淡之雅,构成了宋人之韵。黄庭坚和范温就大谈平淡境界中的“韵”。
凡书画当观韵。(黄庭坚《题摹燕部尚父图》)
山谷之言曰:书画以韵为主……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苟韵不胜,亦亡其美。(范温《潜溪诗眼》)
有余意之谓韵。(范温《潜溪诗眼》)
书法中的平淡之韵,还体现在蔡襄的书法上。蔡书的平淡得到普遍的认可,是一种崇尚平淡厚蕴的士人趣味在宫廷的体现。明代盛时泰《苍润轩碑跋》说:“宋世称能书者,四家独盛。然四家之中,苏(轼)蕴藉,黄(庭坚)流丽,米(芾)峭拔,皆令人敛衽,而蔡公又独以深厚居其上。”[10]所谓蔡襄的深厚,就是士人所推崇的温和、太平、淡泊之美。宋代郑橚《跋蔡君惠书》说:“观蔡襄之书,如读欧阳修之文,端严而不刻,温厚而不犯。太平之气,郁然见于豪楮之间。当时朝廷之盛,盖可想而知也。”[11]
平淡的境界还体现为宋人山水画中的“远”。郭熙《林泉高致》谈到山水画的“三远”:“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溃冲融,而缥缥渺渺。其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淡。”三远形成了一种具有节奏化音乐化的空间。三远,同样是一个充分考虑到主体观赏的审美视线:“正面溪山林木,盘折委曲,铺设其景而来,不厌其详,所以足人目之近寻也;傍边平远,峤岭重叠,钩连缥缈而去,在厌其远,所以极人目之旷望也。”[12]全景山水的组织方法和中国山水的基本原则已经包含在里面了。如果把韩拙对平远进一步深入而论述的阔远、迷远、幽远加进来,把一隅山水的“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再加进来,整个中国山水画的理论就完成了。
三、词曲美学的平淡境界
词,可谓是宋代美学的代表。曲,可谓是元代美学的代表。
关于词的美学,宋代最初是将之作为“诗余”,相当于从“书画一乐”的角度去看。晏几道《小山词自序》:“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13]苏轼《题张子野诗集后》:“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波耳。”[14]因此,其要求的仍是从诗书画美学的延伸。黄庭坚《小山词序》说:“独戏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错,能动摇人心。”[15]张耒《东山词序》说:“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有待雕琢而丽。”[16]在运用“诗余”之论时,也注意到了词的特点。
于是“词别是一家”的理论被提出,李清照《论词》是典型代表,她通过批评什么是不好的词来暗示什么是好的词。首先批评两种不似词的词:一是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以诗为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二是王安石、曾巩等以文为词的词,“人必绝倒,不可读也”。然后批评另外两种是词,但不是理想境界的词:一是柳永的俚俗词,“虽协音律,然词语尘下”,俗气。二是晏几道、秦观、贺铸、黄庭坚的词,各有缺点,“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17]由此可知,李清照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白壁无瑕的富贵佳人,亦即追求的是一种具有词的音乐性的“雅致”境界。
沿着词的特点来讲词而又较为体系的,是沈义父《乐府指迷》和张炎《词源》。二者都回到词的艺术特性上对词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沈义父以周邦彦为理想境界,张炎以姜夔为理想境界,完全和李清照一样,以音律之协谐与内容之雅贵为第一义。坚决反对以诗为词,《乐府指迷》说:“不协律则成长短之诗”[18],《词源》说:“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19]二者的体系性,首先在于结构方面。
《乐府指迷》基本结构为:一,论词四标准(举周邦彦为正面榜样,以康与之、柳永、姜夔、吴文英、施岳、孙惟信为教训),二,词的大结构(起句、过处、结句);三,词的具体技巧(咏物、用事、字面、代字、造句、押韵、去声字、虚字、用人名、腔、句中韵、忌犯)。
《词源》的基本结构为:一,词的大结构(制曲、句法、字面、虚字);二,词的总风格(清空、意趣);三,词的具体技巧(用事、咏物、节序、赋情、离情、令曲、杂论)。
两本著作的主要特点有二:第一,主要论述词这个艺术门类的技术层面,只是按照词的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本性来论述的。对何以应是这些技术,没有进行更深的美学和文化分析。第二,在论述词的风格时,仅在把握词的一般特性,并与时代的审美风尚相汇通,并无独特的深度。《乐府指迷》的四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区别于诗统词派),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区别于世俗派);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无深长之味,(区别于直率);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婉柔之意(区别于豪放)。”[20]不能说不对,都是大白话。《词源》的“清空”“意趣”之论:“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折下来,不成片断。”“词以意为主,如苏东坡《中秋水调歌》、王荆公《金陵桂枝香》、姜白石《暗香》《疏影》,此数词皆清空中有意趣。”[21]这是从美学的境界来讲词境。“清空”使人感到与词与宋代整体风格的相通,与诗的平淡,画的远逸,都有一个对照的关系而相通。“意趣”使人感到与文以意为主,画以意为主,书以意为主相类的宋人腔。由此可见,词的理想境界与宋代美学理想境界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系。
元代陆行直在《词旨》[22]中进一步探讨了词的境界问题。他要求将吴文英的字面、史达祖的法度、姜夔的骚雅、周邦彦的典丽等四个方面结合起来。前两者属于词的形式,后两者属于词的内容。从“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上,要求“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同时还将姜夔词中“孤云野鹤,去留无迹”的“清空”境界,赋予其“命意贵远”的内容,这就又暗通于诗中“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平淡境界了。
元曲,包括作为诗歌形式之散曲,和作为戏曲的杂剧,前者区别于诗和词,有自己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散曲上,后者作为戏曲中的一部分,与整个戏曲的叙事和人物塑造相关。无论在散曲上还是在戏曲上,曲的一个重要美学境界就在于“本色”。可以说,元曲的本色境界是宋人平淡境界的一种继承和转进。
四、音乐美学的平淡境界
宋元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宋以前的中国音乐史主要是宫廷音乐史。自宋代开始,民间俗乐形态成为社会音乐生活的主流。同时,宋代也是雅乐复古的重要时期,可谓是一个雅俗共赏的音乐美学时代。其音乐类型主要有文人音乐、祭祀音乐、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
北宋时,中央乐官机构有:太常所辖太乐局、鼓吹局、教坊;独立于太常的大晟府(北宋末取消);属于黄门乐系统的云韶部;属于军乐系统的西班乐、钧容直。这一音乐体系里面,教坊与在晟府都与词曲创作有关,教坊要王朝庆典撰写“歌乐词”,大晟府由音乐精英组成,虽然主观愿意是要造就时代雅乐,但实际上作出的是“近乎民间俗乐的音乐体系”[23]。按音乐要求做词,是其主要任务之一。
《宋史·乐志》记载:“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坐,宰相进酒,庭中吹华案。第一,皇帝再举酒,群臣立于席后,乐以歌起。第三,如第一之制。第四,皇帝举酒,百戏皆作。第五,皇帝举酒,如第一之制。第六,皇帝举酒,乐下致辞。第七,合奏大曲。第八,皇帝举酒,殿上独弹琵琶。第九,小儿队舞。第十,杂剧,罢,皇帝更衣。第十一,皇帝再坐,殿上独吹笙。第十二,蹦掬。第十三,皇帝举酒,殿上独弹筝。第十四,女弟子队舞。第十五,杂剧。第十六,皇帝举酒,如第一之制。第十七,皇帝举酒,奏鼓吹曲。第十八,皇帝举酒,如第一之制。第十九,用角抵,宴毕。”[24]由此可见,宫廷宴乐已经大大地按照时尚趣味进行。宋代都市里,瓦舍勾栏群立,诸宫调、杂剧话本、百戏等民间艺术,一片繁胜。都市音乐的主体,一是词曲,二是宫调。而与士人精神相关的琴,也呈现多种风格,宋代政和年间的成玉涧《琴论》说:“京师、两浙、江西,能琴者极多,然指法各有不同。京师过于刚劲,江西失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25]在这多元并立的乐论之中,从传统乐论和士人趣味的结合看,仍然流动有与平淡总体美学相契和理论。
从乐的本体来讲,应有“淡泊平和”的境界。
周敦颐就是从传统乐论而得到平淡境界:“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通书·乐上》)欧阳修同样把“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看成是由古而来的“纯古淡泊”之境,认为与琴之乐相关联,可以“平其心”[26](《送杨置序》)。
进入到时尚词曲,则应讲究“字声谐和”效果。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乐律二》说:
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韫,谓之“叫曲。”
从律的角度讲,要求“中声为定”。朱熹在讨论乐律与古尺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律管只吹得中声为定”。“律管只吹得中声为定。季通尝截小竹吹之,可验。若谓用周尺,或羊头山黍,虽应准则,不得中声,终不是。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牛鸣盎中”,谓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勖造于晋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和岘造于周世宗时,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圣特异,初不曾理会乐,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声遂和。唐太宗所定乐及本朝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笑云:“如此议论,又却似在乐不在德也。”(《朱子语类》卷92)在此,“中声”、“平和”成为了朱熹音乐美学追求的审美理想与境界。
从琴的角度看,则应有“主客尽和”之境界。
朱长文(1039—1098)《琴史·尽美》说“琴有四美:一日良质,二日善斫,三日妙指,四日正心。”[27]四方面都是重要的:“是故良质而遇善斫,善斫既成而得妙指,妙指既调而资于正,后为天下之善琴也。”所谓“善琴”,即“感格幽冥,充被万物”天地万物之声皆在其中矣。朱长文说,所谓天地万物之声,正如圣人之作琴,在“参弹复徽,攫、援、標、拂”的妙指之下,“尽其和以穷其变,汲之而愈清,味之而无厌……尽雅琴之所蕴”。这里,和、清、味、蕴,提倡的也是一种平淡之境。
然而,平淡更是一种心灵境界。
欧阳修就是这样看琴的审美的,在《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之一)中讲:“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心意煮既得形骸忘,不觉天地白日愁云阴。”[28]苏轼《听僧昭素琴》说:“至和无攫醉,至平无按抑。不知微妙声,究竟从何出。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复此微吟”。[29]琴的境界不在于琴,也不在于声,而在于心,淡泊的关键在心灵。真德秀《送萧道士序》说:“琴以养吾之心而吾本无心,终日弹而日未尝弹可也;诗以畅吾之情而吾本无情,虽终日吟而日未尝吟可也。”[30]所谓无情无心,正是超出了日常之情和日常之心,而达到与天地同一的道心。这正是古人讲的:乐者,天人之和也。
五、设计美学的平淡境界
宋辽金元时代,设计美学思想甚多,然而其主导在于“适宜”的设计美学的平淡境界追求。
范仲淹(989—1052)是开启宋代设计新思想的第一人。他所所崇尚的“制器尚象”设计理想成为了有宋一代设计的基本精神。他在《制器尚象赋》中,对《周易》以来的“制器尚象”思想,作了实用精神的解释:主张“器乃适时之用,象惟见意之筌”的原则。《水车赋》中,对水车这种提水工具,提出“器以象制,水以轮济”的原则。同时把水车放入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合一之中:“智者乐水而起予,梓人治材而和汝”。在《铸剑㦸为农器赋》对以前战争时期的“锋镝”,成了现在和平时期的“镃錤”,强调了事物的“备物致用”原则。
欧阳修在设计思想方面,继承了“制器尚象”的精神,同时又进一步提出了“反朴归醇”、“革故取新”的设计主张,以反对当时的不实浮夸,过于粉饰的设计思想。在《斫雕为朴赋》中,欧阳修提倡“除去文饰,归彼淳朴”的设计思想,追求“防世伪者在塞其源,全物性者必反其所”、“归璞玉以全真”的审美理想。主张“淳自浇散,器随朴分”。在《大匠诲人以规矩赋》中,欧阳修则提倡“运斤取法,必先正于圆方”的观点;还认为“匠之心也,本乎天巧;工之事也,作于圣人”,由此突出了设计造物活动的本体与宇宙本体的一致性(本乎天巧),提升了设计活动的神圣地位(作于圣人)。
王安石在设计思想方面,强调器物设计“以适用为本”,是对范仲淹注重实用、崇尚理性设计精神的弘扬与推进。特别是王安石所推行的改革直接影响了《营造法式》设计思想的形成和展开。
朱熹在《家礼》中设计一个有强烈时代感的祥和的社会秩序。要求改革了古代礼制中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诸多弊端,努力设计出一套服务于大众的《家礼》。这种礼就不再是只为上层社会所专用的“贵族之礼”,而是通用于整个社会的、更多地考虑到社会普通家庭的“庶民之礼”。这一重大改革是整个宋代注重务实设计精神的体现。这一设计思想主要表现在“祠堂制度”、“深衣制度”等方面。而“祠堂制度”是朱熹为大众最为成功地设计的生活方式之一。此外,在朱熹众多著述中表现出了设计“以适用为本”、“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祠堂”通过祖先、家谱,由家而族而社会,形成一种人伦秩序。“祠堂”在宋以后中国乃至东亚诸国的产生了巨大影响。“服饰”的变化是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朱熹十分关注这一事实。他对“深衣制度”的改革,使得远古神圣的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且原本远离普通人生活的“深衣”第一次“大众化”、“现实化”,成为了普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朱子语类》中,朱熹论述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服饰也会相应变化。服饰的变化其核心也就是服饰设计理念的变化,设计理念直接表现在具体设计形式的创新上。如“背子”这一服饰设计,是宋以前所没有的设计款式,而是随着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产生的新的设计形式。关于服饰的变化还体现在外来文化的冲击。如“胡服”,就是一种不同于“汉服”的异族服饰设计款式,自晋以来,“胡服”广为华夏民族所喜爱,乃至于宋代的服饰主流“大抵皆胡服”。
薛景石的《梓人遗制》是我国古代介绍以木材为主要制造材料的机械设计及其方法的专著。以介绍古代机械的形式、结构、设计方法和制造方法为主。薛景石不仅懂得机械制作的理论,而且能在进行机械设计的过程中有所创新。在机械制造的过程中非常注视图样的绘制与应用。在制作中“求器图之所自起,参以时制而为之图”,从而把图样作为表达设计思想、修改设计的工具。《梓人遗制》的设计图样不仅有总装图,而且还包括部件图和零件图,即所谓“每一器,必离析其体而缕数之。分则各有其名,合则共成一器。规矩、尺度各疏其下,使攻木者揽焉。所得可十九矣”。书中共有图样十二幅。这些图绘制详明,是一部难得的古代机械设计制造图册。
黄道婆在织布机械方面的设计。据《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记载,黄道婆因为发明并教授“捍弹纺织之具”而造福和享名一方。这是一整套织布工艺流程。“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31]充分展示了传统“女红”审美设计文化的魅力。
宋代设计美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李诫(1035~1110)的《营造法式》。《营造法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营造设计理论专著,堪称中国古代设计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之一。《法式》继承了《易》《礼》体系设计美学精神,对《考工记》为核心的设计美学思想进行了历史性总结,同时充分反映了唐宋建筑设计实践经验的理论成果,并构建起了一个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设计理论体系。[32]《营造法式》的设计美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设计制度美学。制度美学在《营造法式》中体现为两个层次:首先是建筑与礼制结合,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审美物化,强调“菲食卑宫”,追求“淳风”之审美平淡境界;其次是对建筑本身设计制度的美学要求,这是对设计与建筑的实施过程予以标准化控制,如“材分制”、“等第”等。二是结构设计美学,主要体现在“大木作”、“壕寨”等篇章中,强调建筑设计本体性的空间构建的功能性问题,因此结构功能美是建筑设计美学的第一要素。三是装饰设计美学。主要体现“小木作”、“彩画作”等篇目中,突出了人居环境的精神性层面——装饰性设计。具体涉及到形式美问题,如“生起”、“卷杀”、“举折”、“侧脚”等造型艺术手法,以及“彩画”中的各种色彩搭配原则、纹样设计规律等。其中“彩画”中的“碾玉装”类型充分显示了平淡审美境界追求。
注释:
[1][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0年版。
[2]《书黄子思诗集后》《苏轼文集》卷67,中华书局1986年版。
[3]《评韩柳诗》《苏轼文集》卷67,中华书局1986年版。
[4]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竹坡诗话》,中华书局1980年版。
[5]《朱熹集》卷64。朱熹此语出自晋陆机《文赋》:“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
[6]《鉴画》《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30,中国书店1992年版。
[7]《米芾集·书画论集·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 [宋]黃彻:《拱溪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9] [宋]陈俊卿:《拱溪诗话序》,《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转引自朱仁夫《中国古代书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345页。
[11][宋]郑肃:《栟榈集》卷二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2][宋]郭思《林泉高致•山水训》,明刻百川学海本。
[13]《全宋文》卷1664(第76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4]《苏轼文集》第6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46页。
[15][宋]黄庭坚:《小山集序》《黄庭坚全集》(刘林、李勇先、王蓉贵点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1984年版。
[17]《李清照集笺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8][宋]沈义父:《乐府指迷笺释》(蔡松云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19] [宋]张炎:《词源注》(夏承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20] [宋]沈义父:《乐府指迷笺释》(蔡松云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21] [宋]张炎:《词源注》(夏承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22] [元]陆辅之撰,[清]胡元仪释,[民国]陈去病补释《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词类•词旨》,辽宁省图书馆藏民国陈氏排印笠泽词徵付印本影印。
[23]龙建国《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
[24]元·脱脱等《宋史·志第九十五》中华书局简体版,1999年版。
[25][明]蒋克谦:《琴书大全》(见《琴曲集成》第五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
[26][宋]欧阳修:《欧阳修诗文校笺》卷4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7][宋]朱长文:《琴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
[28]《欧阳修全集》卷四,中华书局2001年版。
[29]《苏轼诗集》卷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
[30]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8,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31]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中华书局2004年版。
[32]关于《营造法式》设计理论体系等问题,可参见邹其昌《〈营造法式〉艺术设计思想研究论纲》清华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5、《营造法式·出版说明》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2010年第二版、或邹其昌《〈营造法式〉建筑设计理论体系的当代建构》《创意与设计》2012-04。
注: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美学史》(马工程)重点教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JZDMG026;项目首席专家为张法教授,本人作为核心专家,承担宋辽金元部分的写作)。原载《创意与设计》2013(04)
转自设计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