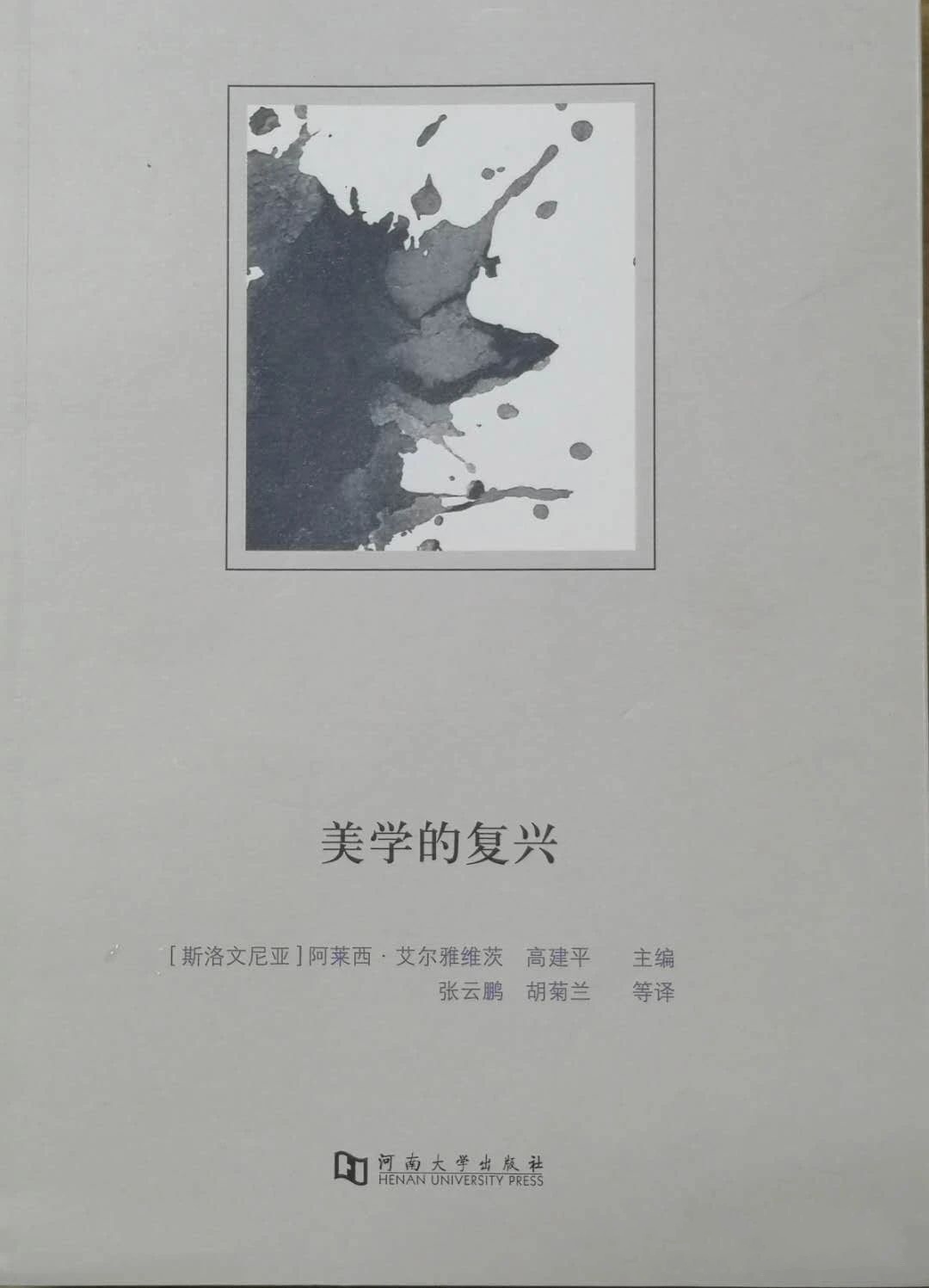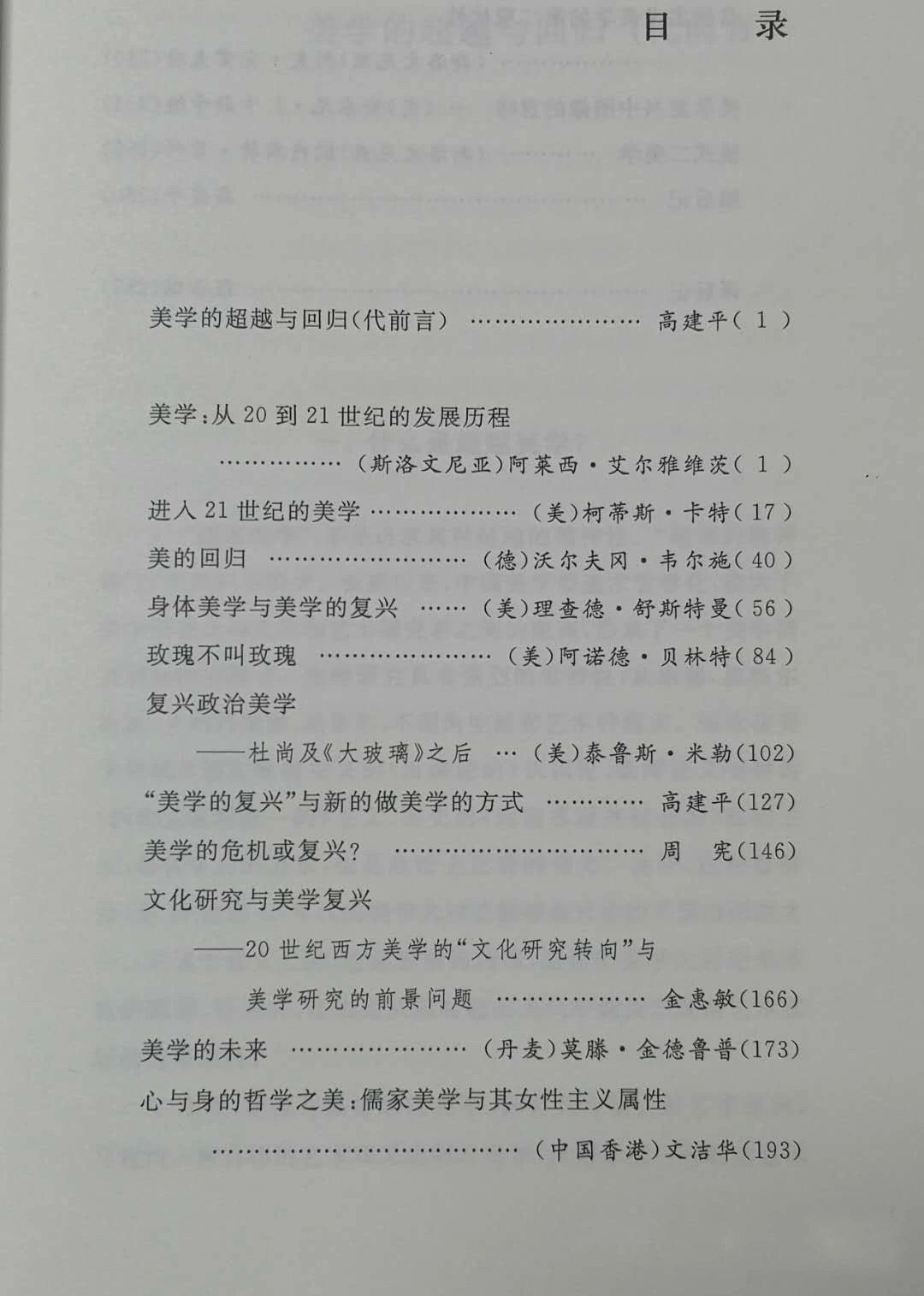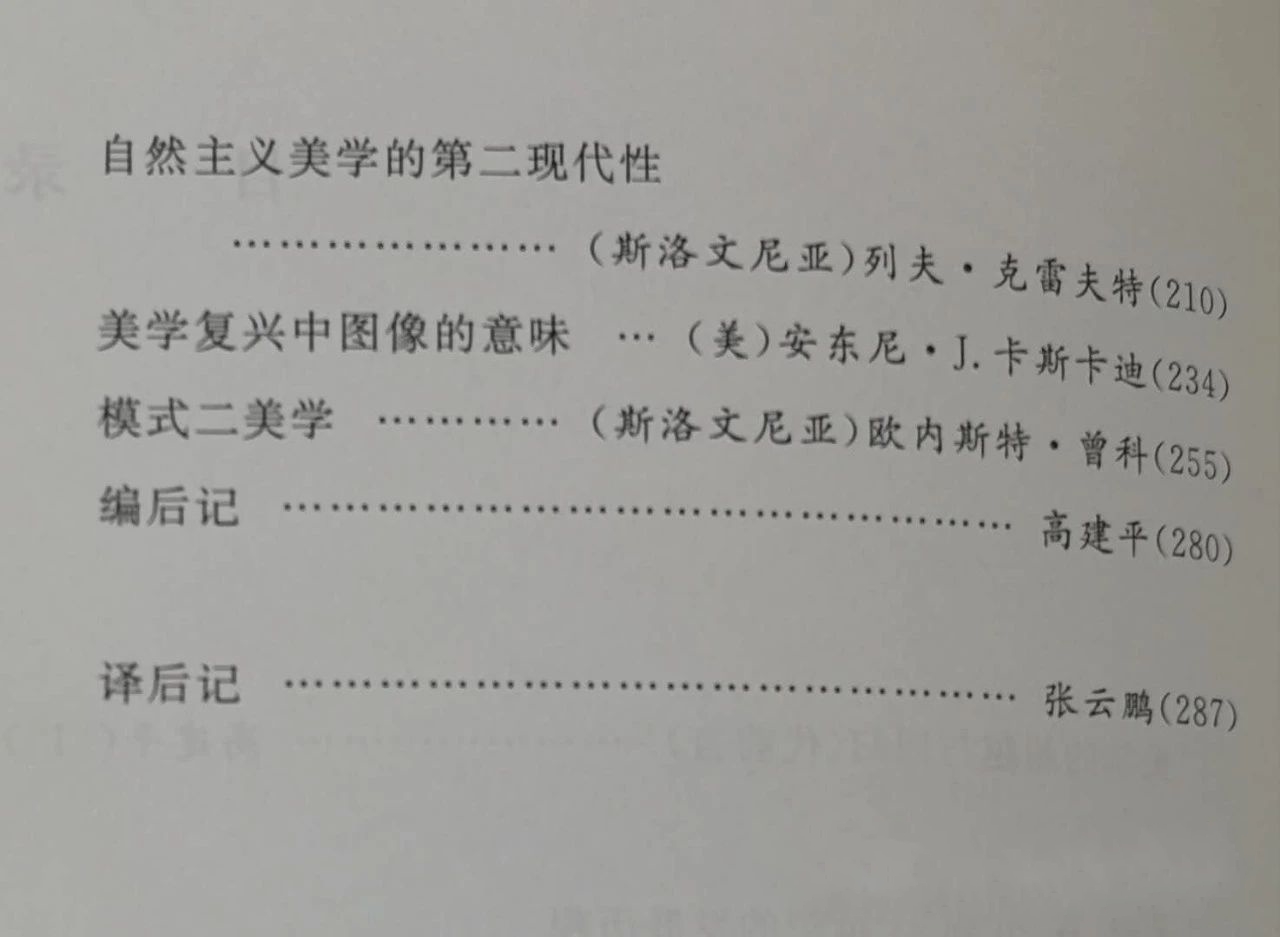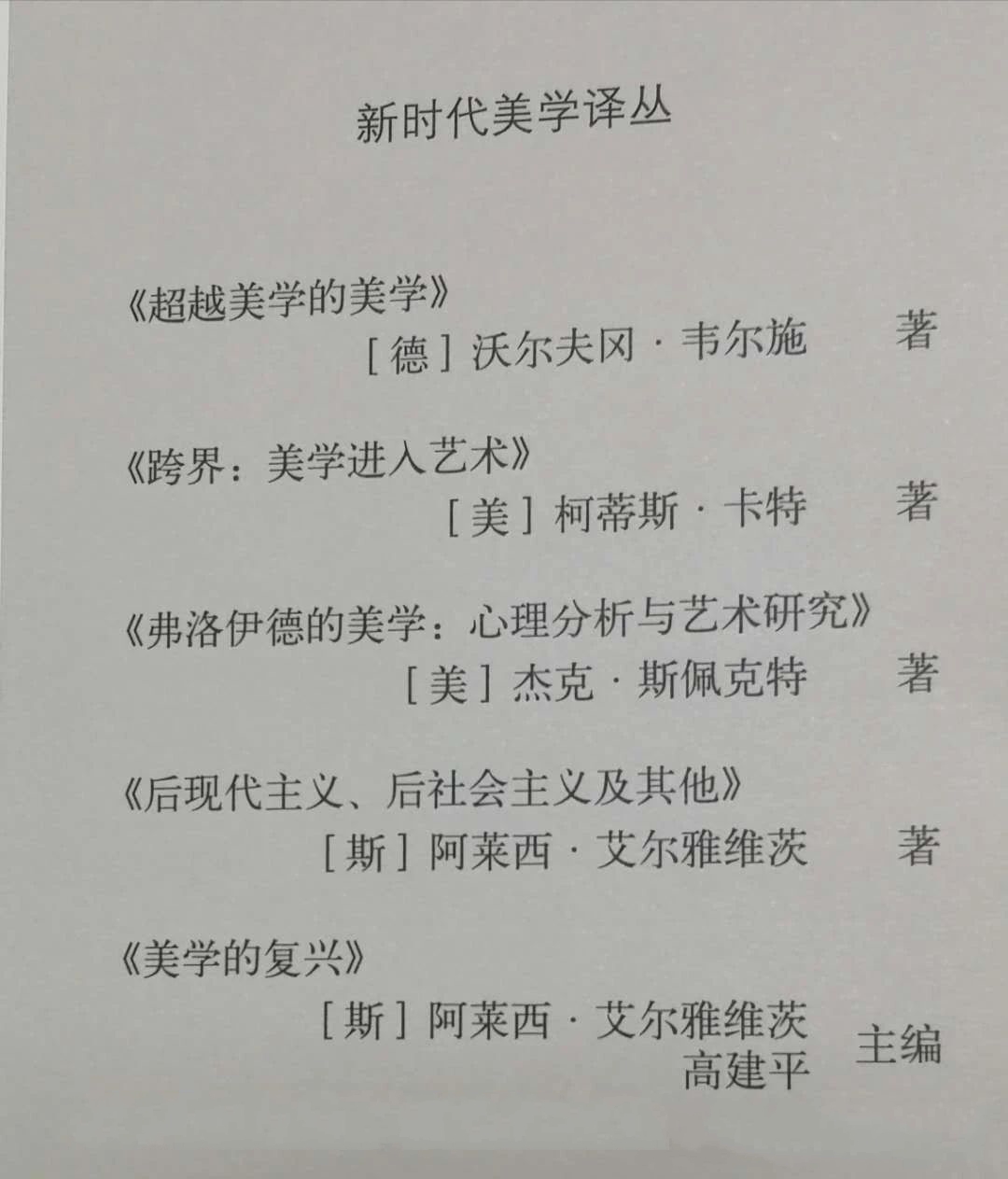高建平
记得是2007年,我与阿列西·艾尔雅维奇一道,坐在卢布尔雅那河边的一间办公室里,谈论美学的复兴话题,商定要编这个文集。他后来很快就约了一些稿件,而我负责中文的稿件的邀约,编辑和翻译。这项议论多年的工程,到现在才完成,实在是我做事太拖拉,与阿列西的风格恰成对照。好在美学的复兴是一个过程。前几年说复兴,有人反对,还在说“美学已乘黄鹤去”,“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几年,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一些反对声音也冷却下来,到了“复兴”的深化期,介绍一些世界各国美学家对“复兴”的状态描述和原因揭示,也许正逢其时。
“美学的复兴”这个话题我在1995年芬兰拉赫底会议上提过。当时,我说,80年代时,美学在中国“热”过,后来就冷了,它终究还会再“热”起来的。到2002年我在北京的“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会上发言时提出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观点时,建立新时代的中国美学的观点,已经比较清晰。2010年8月在北京开第18世界美学大会,面对着近千人参加的美学的盛况,我也兴奋起来,说了一句:中国的美学家们,不能继续像“白头宫女”“闲坐说玄宗”那样,追忆过去的盛世,津津乐道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在新世纪创造美学的新辉煌。
的确,时至今日,谈论美学复兴的时机已经成熟。学界谈论美学的人越来越多了,美学的书也越出越多了。今天,美学的黄鹤是不是会飞回来,已经不再是问题。相反,为什么会飞回来,才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编这本书,就是想为之提供新的视角,试图说明,在不同的国家,美学由于不同的机缘而复兴。
在中国,美学复兴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条:
第一,80年代的美学热,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被经济大潮卷走的。在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经济就成了“主战场”。此后的种种社会改革和人的观念的变化,都呈现出由经济发展“倒逼”的现象。“倒逼”有其好处,阻力小,水到渠成。“倒逼”也有不好之处。水到实际上不能成渠,要等到淹坏庄稼,闹了洪水后,才能冲刷成渠,社会成本太大。因此,还是要先挖渠后引水。单一经济驱动的改革,逐渐走到了尽头。近年来,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都在逐渐摆脱等待经济的发展来“倒逼”的思路,形成新的“顶层设计”。在这时,人的素质的发展,教育从工具性向人文性的转化,将一个没有直接功利性,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这就是人的品味建设。品味建设是提高人的修养的需要,也与社会建设联系在一起。古希腊人通过戏剧进行城邦公民的人文品味建设,现代社会也需要通过审美教育,实现品味建设的现代化。美学的作用也这时被重新发现。
第二,20世纪的西方美学有一个与艺术密切联系,试图对先锋艺术和此后的各种新先锋艺术、后先锋艺术进行解释的传统。这种解释,被看成是艺术日益哲学化的表现。然而,上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和80年代的“美学热”,都与同时代的中国艺术保持较远的距离,也与当时正在西方国家兴盛的先锋艺术没有什么关系。到了90年代,中国的先锋艺术在迅猛发展,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这时,中国当代艺术与理论的脱节现象,也就日益显示出来。结合发展着的中国艺术加强美学研究,成为时代的要求。中国艺术的发展需要引进新的美学理论,也需要中国美学家们走近艺术,使理论真正从艺术中生长起来。艺术的发展呼唤着美学和艺术理论,没有理论,艺术中的任何新创意,都只是过眼烟云的现象,不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美学的要求。
有一个被人们多次提到的时髦的话题:日常生活审美化。现代技术和工艺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竞争要求,使得从产品到生活环境都被彻底美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对生产和生活从审美维度进行思考的要求。
还有一个人们正在进行热烈讨论的话题:美与生态。符合人的生态观念的事物为什么就是美的?我们是把人类对生态保护的理解投射到对象上去,还是生态规律与审美的规律有一种天然的对应性?当人们在说符合生态观念的对象是美的时,他们是在阐释一条原理,还是在宣传一种信念?如此等等,尽管其中存在着许多理论的问题,生态需要保护的现实刺激了生态美学的发展。
近年来,一个更新的话题受到人们的关注:城市。我们会发现,自然美的对象,不再只是乡间的小溪,金色的麦浪,或者浩翰的大海,巍峨的高山。城市的天际线也可以产生节奏感,生长着的城市本身也能成为活的艺术品。当中国在迅速实现着城市化,老城被改造,新城在变高变胖时,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是人们在其中居住,不管是否喜欢也被强迫每天都观看,甚至在影响自己日常生活的心情,以致于塑造我们的后代的个性的地方。城市建得怎么样,自然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城市不能只是方便、宜居,还要使人看上去舒畅,引以为自豪。美学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集点。
如此等等,在上世纪的80至90年代之交,曾经有太多的理由,要宣布美学的过时,而到了世纪之交,又出现了太多的理由,要呼唤美学的复兴。经过了这个学科被冰封的时代,中国学界终于发现,美学的温暖可以融冰。美学与我们的生活和艺术,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和未来的梦,都息息相关。
在西方,美学度过了上世纪后半期的一些困惑,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也逐渐升温。其原因也是多种多样,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条:
康德美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在20世纪一直面临挑战。审美是不是无功利?艺术是不是自律?这些命题一直受到学界的挑战。但是挑战归挑战,康德美学实际上一直占据着美学的主流。20世纪初美学的心理学转向,变成了美学沿着康德的线索向前深化,把一个哲学话题变成科学或准科学的话题。20世纪中叶的语言学转向,特别是分析美学,只是逃避而非面对康德美学,使美学变成了只是概念分析,与艺术保持一种间接性。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曾致力于批判康德美学,但这种美学长期受忽视,直到世纪后期才重回主流。由于种种的机缘,直到20世纪末和新世纪之初,建立超越美学的美学的意识,才逐渐被人们提了出来。超越美学的美学,是说超越了康德的美学,但不是完全走出美学本身,而是走出去再回来,重建康德之外的美学。
当代西方美学界,当然仍在面向艺术。但是,超出了分析美学的西方美学界,不再只是寻找艺术的定义。艺术的定义引导人们进行概念性的探讨,而20世纪末和21世纪之初的美学,更加面向现实。这时,一个更加直观的话题被人们提了出来:艺术的边界。什么物品是艺术,什么不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念引导人们得出一个结论:所有物品都是艺术品,所有的人都是艺术家。的确,所有的物品,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由于特定的阐释,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品,因此,人的所有制作活动,也都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中,由于特定的阐释而成为艺术活动。这种艺术边界模糊的状态,在一些不愿作深入反思,只认可现象的艺术家那里,在受到新时代新现象的震憾,欢欣鼓舞地去拥抱或不知所措而困惑的文化研究者那里,形成了艺术边界取消论。然而,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边界的模糊,是说边界需要调整,而不是取消。超越美学的美学,是说,传统的美学被超越了,我们还是需要建立起新的美学来,要对艺术问题作出回答。
当代西方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视觉艺术的转向。由于图像技术、互联网、市场经济在背后的操控、消费主义的盛行,视觉的优势地位得到了确立。美学不是为这种现象唱赞歌的。将这种现象描绘一遍,没有什么意义。美学所要做的事,是指出这种发展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弊端,说明视觉与听觉,感知与意义,直觉与理解之间的平衡关系,说明一种新感性的建立,不是在于感觉的描述,而是在于感觉的改造。
最后是救赎问题。救赎本来是一个宗教话题,面对当代社会的种种弊端,有一些美学家们提出了艺术的救赎之道。黑格尔曾排列过艺术、宗教、哲学的精神向上发展三步骤,但是,相反的发展路径可能也能成立,即抽象的哲学说教被更富情感色彩的宗教宣传所取代,进而在宗教淡化后,一些原本的宗教艺术,如宗教建筑、绘画、雕塑、音乐和舞蹈等,变成了世俗的欣赏对象。艺术继续在生活中起着作用,但它只是生活的改造,而不是救赎。
种种的变化,给美学带来众多的话题,从而也促使美学这个学科再次被人们所记起,为社会所需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美学不只是欧洲的学问,也应该是世界的学问;美学也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美学复兴的机缘。
最后,再谈谈美学在一些非西方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有一个明显的18世纪在欧洲的一些国家起源,再向一些非西方国家传播的情况。这一过程,在像中国、日本、韩国这样一些国家,在20世纪就完成了。在这些国家,美学这个学科传入以后,各自与自身的艺术、生活和哲学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美学。同时,在这些国家,人们倾注着甚至比在西欧国家更多的热情。正像一本书会有自己的命运一样,一个学科也有自己的命运。美学来到东亚,找到了适宜的土壤,长势良好。
然而,这一学科传播的历史并未完成。这些年,美学这个学科及相关的组织在拉丁美洲、西亚、非洲,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陆续建立起来,与各自的本土传统,地方资源结合,形成美学的新发展和新形态。高山上的尼泊尔派人参加世界美学大会,伊朗学者邀请一些美学家去讲当代美学,来自南非和肯尼亚的学者开始对愿意与国际美学界交往,这些迹象都是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新机遇。美学之花要到更多好田里去栽种。
喜爱这个学科,期待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学科,希望有更多地区的人以这个学科为平台进行交流,这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的更大梦想是,这个学科的研究能为文明建设,为社会进步提供灵感源和动力源。
高建平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