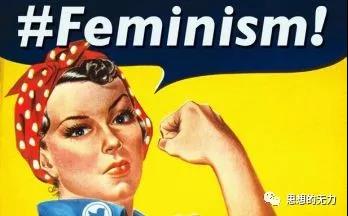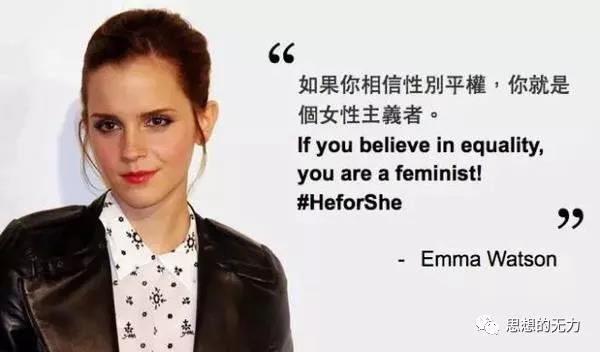王晓华
本文原载《南国学术》(澳门)2014年第4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美学》2015年第2期全文转载。
在当代西方大众文化领域,有关身体的审美理想依旧显现出不可忽略的性别差异,诸如男性精神和女性气质之类言说仍未绝迹。尽管遭遇到了持续的解构,这套话语体系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日常生活、商业运作、意识形态。事实上,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背景:自古希腊起,依据身体的自然(性属)-社会(性别)特征,西方美学就建构出了等级制的话语体系,最终将男人和女人纳入不同的审美范畴,形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二分法。回顾、梳理、重构这套话语产生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至今仍支配文化生产的某些基本范型。
一
既强调身体的性属(gender),又试图超越社会学维度的藩篱,乃当代女性主义(feminism)的重要特征。[①]在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克里斯托娃(Julia Kristeva)、巴特勒(Judith Batler)等人的著作中,男/女二分法均为解构的对象。解构的对象是已经建构出的体系。没有建构,解构就无从谈起。当女性主义试图解构诸如此类的二分法时,一个相应的建构过程也被逐渐敞开。就西方美学史而言,与身体性别相关的基本建构日益清晰可见。
现代流行的男/女二分法源于父权制体系。随着父权制的崛起,性别关系的天平迅速向男人倾斜:“身体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规律性,通过将妇女从最高级的任务中排除出去,将低级的位置分配给她们”。[②]于是,“社会与整体宇宙都分两边,一边是神圣、高贵和珍奇的,另一边是凡俗、平常的;一边是男性的,坚强而主动,另一边是女性的,软弱而被动……”。[③]从古希腊开始,这种社会配置就强调先天差别,试图将等级制归结为自然的安排:
这是劳动的性别分工,是对两性承担的活动及其地点、时间、工具的严格的分配;这是空间的结构,存在着男女对立,大庭广众或市场专属男人,家庭专属女人,或在家庭内部,炉火归男人,牲畜棚、水和植物归女人;这是时间的结构,劳动日、耕地年、或生命的循环、中断的时刻是男人的,漫长的妊娠期是女人的。[④]
根据柏拉图(Plato)转述的古希腊神话,男人和女人分别来自太阳和大地,其地位差异不言而喻。[⑤]在《理想国》(Republic)中,柏拉图将女人定位为“较弱的性别”(weaker sex),强调“雄性更强壮”。(Republic 451e)[⑥]写作《政治学》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也说:男人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能处于最完善状态,但女性相对低下,因此,强者统治弱者乃理所当然之事。(Politics 1254a5)[⑦]
随着这种定位日益清晰,性别层面的审美也开始出现分化。男性之美更多地意味着力量、勇敢、英武之气、蔑视苦难的精神、旺盛的生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壮:
对于青年人来说,美就是拥有身体上的适宜,以便忍受奔跑时的努力和力量上的竞争;这意味着他看起来舒服;故而适应力量和速度竞赛的全能运动员是最美的。就一个壮年男子而言,美就是适合战时的努力,好看但具有令人生畏的外表。到了老年阶段,美就是强壮到足以应付必要之事,远离造成他人痛苦的畸形。[⑧]
强壮意味着力量,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移动其他事物:推、拉、举、戳、抓,等等。显然,这是一种属于运动员、战士、劳动者的美。它更多地显现为突出的尺寸、力量、敏捷。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娴静是女人的光荣”。[⑨]作为“较弱的性别”,女人只能承担“较轻的工作”。(Republic 457a)[⑩]面对掌握权力的男性,她们必须学会服从,展现柔顺的动姿。于是,诸如“女人气”之类话题已经出现。[11]在米南达的剧本中,读者甚至可以发现“可爱的面孔”和“甜美的声音”等针对女性的描述。[12]
吊诡的是,此类言说并不多见,聚焦女性的身体美学并未因此诞生。由于不能参与公共生活(如当将军、政治家、陪审员),女性身体事实上处于隐匿状态,很难进入大众的视野,因此,作为一个性属-性别的她们并非重要的审美对象。[13]在审美领域,她们被覆盖和遮蔽:“古希腊人认为理想的美体现在青少年身上”,“大量的花瓶上刻有‘漂亮的少年’字样,而‘漂亮的少女’则较少见。”[14]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曾经兴致勃勃地提到雅典人对美少年的偏爱:“你没看到人们说塌鼻子的‘容貌俏丽’,高鼻子‘仪表堂堂’,鼻子不高不低的则‘长得恰到好处’?”(Republic 474d)[15]如此说话的他关注的是男性,女人的美则难入他的法眼。对于他来说,女性虽然属于“较弱的性别”,但仍然应该像男人一样被对待:“在教育问题上和在别的事情上,女性一定要和男性结合在一起。”(《法篇》805c);“立法者应当彻底,不能半心半意,他一定不能在为男性立法后,就把另一种性别的人当作放荡的奢侈生活和工具和取乐的对象,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整个社会的幸福生活只剩下一半。”(《法篇》806c)[16]这种考虑的核心并非女性的福祉,而是其社会功能:“如果城邦的妇女没有训练好,乃至于连母鸡面对最危险的野兽或其他任何危险冒死保护小鸡的勇气都没有,如果她们只是朝着神庙狂奔,坐在祭坛和神龛前,那么这种表现确实是城邦的奇耻大辱,是人类最卑贱的表现。”(《法篇》814b)[17]柏拉图所在的雅典人口并不众多,小国寡民的现实处境使他不能过于强调男女之别,否则,本就不大的城邦就会只剩下一半的劳动力。古希腊的女性虽然被限制在家庭中,但仍需部分参与城邦的物质生产。正因为如此,古希腊思想家倾向于建构统一的身体美学。譬如,写作《修辞学》时,亚里士多德主张“男人和女人”应该具有“共同的优点”:其一,所有青年人身体上的优点是身材高大、漂亮、强壮、善于运动,“灵魂上的优点则是自治和勇敢”;其二,“对于女性来说,身体上的优点包括美丽和高大;灵魂上的优点是自治,勤劳而不利欲熏心。”(Rhetoric,1361a)[18]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他又曾提到:“如若状况良好是指肌肉的结实,那么,状况不佳必定是指肌肉的衰弱。要造成良好的身体,就在于使肌肉结实。”(《尼各马科伦理学》1129a)[19]显然,这是一种以男人为样板的身体美学。男人被树立为典范,女性则不过是难以成功的效仿者。有关男性的审美尺度被扩展到女性身上,规范和引领她们,但又同时显露其欠缺。在审美场域中,她们被男性巨大的身影覆盖了,处于从属地位。
总的来说,古希腊身体美学的性别之维没有充分敞开。于是,一个悖论被遮蔽了:如果存在“较弱的性别”,那么,相对应的身体审美尺度就应该有所区别;倘若存在统一的身体美学准则,那么,性别的强弱之分就不具有合法性。不过,由于政治经济学上的原因,这个悖论迟迟未能凸显出来。基督教诞生之后,情况大体上依旧如此。由于动乱频繁,古罗马和中世纪的思想家同样很少聚焦性别上的差异。出于文化谱系上的认同感,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都继承了古希腊身体美学的基本立场:既维系性别维度的等级制,又泛泛地谈论人类身体。在奥古斯丁(AureliusAugustine)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中,我们就可以看待一种具有内在紧张的定位:当亚当(Adam)沉睡时,上帝用其软肋创造了女人,故而女性身体天然地具有从属品格,但二者本性上的一致却获得了保证。[20]因此之故,女性身体同样会复活,荣升为不朽的存在,获得全新的美。[21]出于这种立场,他基本上不专门讨论性别问题。其《上帝之城》乃煌煌巨著,却只在书的最后一章(Book xxii17)用很少的篇幅阐释女性的身体。在他看来,男女身体的美都在于合适的比例和悦目的颜色,其本性并无二致。[22]与奥古斯丁一样,(Saint Thomas Aquinas)将男人和女人都定义为“身魂综体”:“首先,在《圣经》中,纯粹的精神性生物叫做天使;其次,完全肉身性的生物;第三,肉身和精神性的组合物,这就是人。”[23]就此而言,男性与女性并无本质的不同。不过,这并无意味着任何差异都未显现。在《忏悔录》(Confessions)中,奥古斯丁曾如此赞誉自己的母亲:“她穿着女人的衣服,但在信仰上却是个大丈夫。”[24]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定位:男性(man)是人类的代表,优秀的女性像他一样行事,因此,身体的等级制实属合理之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妇女的最高称颂是:“她们有男人的精神和勇气。”[25]亦即,只有成为“女丈夫”(女汉子),她们才会被视为人中翘楚。这等于说:女人越是否定自己,就越伟大。这是一种以男人为范型的性别观念。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种等级关系,英国17世纪的伟大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才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借夏娃之口说:
我的作者和总官呀,凡是你吩咐的,
我百依百顺,这是上帝的规定:
神的话是你的律令,你的话是我的律令,
不要再求知,女子无才便是德。[26]
《失乐园》中的夏娃不仅天生具有从属性,而且是男人亚当的双重创伤:作为身体,她是亚当的伤口(肋骨的创伤);在精神上,她由于意志不坚定,偷吃了智慧果,导致了人类的堕落,是原罪的直接造就者和承担者。正如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等级关系,男人与女人也是不平等的。如此说话的弥尔顿敞开了中世纪身体美学的内在逻辑。当然,此为后话:在古罗马和中世纪的相关话语中,这些推论都未展开,身体美学的性别维度则处于蛰伏状态。
二
弥尔顿生活于17世纪。此时,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观念业已获得广泛播撒。然而,恰在这样的语境中,他说出了具有等级制意味的话语。事实上,这并不难以理解:个体解放的逻辑并非一开始就落实到所有维度,相反,历史的发展显现出明晰的阶段性。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考证,在走向自由的过程中,首先获得解放的是没有财产的男人,妇女、然后是小孩、奴隶、动物。[27]从身体美学的角度看,这个过程同样具有吊诡品格:
欧洲个人的解放,是在一种广泛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在物质的外在强制力变得越来越微弱的时候,它使“获得解放者”的内在裂痕变得越来越大。遭到剥削的身体被确定为“恶”,而上层人可以自由分享的精神却被说成是最高的善。经过这个过程,欧洲的文化发展到了顶峰,然而,人们对开始就已败露的阴谋诡计所产生的怀疑,恰恰强化了人们与身体之间的爱憎关系。[28]
作为社会运动的结果,身体的等级制也以一种近乎悖理的方式被敞开:其一,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迅速走向繁荣,民众生活渐趋优裕,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拥有闲暇时间的女性,衬托男性成为一种事业。;其二,随着解放进程的持续,女性开始大量走入公共空间,成为审美的对象,但等级制的逻辑又凸显她们的客体性。于是,一个背反式的局面出现了:一方面,女性终于结束了自己在审美场域中被忽略、隐匿、遮蔽的状态;另一方面,她们的出场仪式却洋溢着压抑的气氛,审美的性别维度则被强调和合法化。从身体性别的角度看,文艺复兴无疑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文艺复兴时期,大量走入公共空间的女性发现自己身处矛盾的语境中:就现代性的主导原则而言,她们似乎应该与男人平起平坐,但整个社会依然延续了父权制的基本结构。在男人占据了大多数重要位置的世界上,作为一个性属-性别的她们很难立刻分享权力。即使是上层社会的妇女,其主要作用不过是“对男子中的有名人物施加影响和节制男性的冲动”。[29]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女性的解放进程依旧路途曲折,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大体上宣告完成。在此间的数百年中,她们不得不忍受政治、社会、经济、伦理层面的不平等。到了19世纪,英国女作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依旧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一个性别是如此富有而另一个性别却是如此贫穷?”[30]“富有”的性别拥有财产和权力,“贫穷”的性别则必须仰仗男人。如果说前者是主体,那么,后者就是被统治、规定、观照的对象。在社会生活中,男性掌握评审权,他们在女人身上“发现”美。只有被男性青睐,女人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女性最伟大的学问,其内容更多地是人,而且是人类中的男人。”[31]换句话说,“女人的命运和她唯一的光荣,就是使男人心动。”[32]要打动掌控评审权的男性,就必须凸显自己的客体品格,展示自己与之互补的特征:“女人比男人弱小;她的肌肉拥有的力量小,红血球少,肺活量也小;她跑得慢些,抬得动的东西轻些,几乎没有哪一种运动她可以同男人竞争;她不能同男人搏斗。”[33]于是,到了17-18世纪,西方美学的性别维度开始出现明显分化:“男人要有力量型的强壮的身体,布满胡须的下巴和腮帮、粗糙增厚的皮肤,因为男人的习性和身体要有庄严、严厉、果敢和成熟相伴。”[34];与此相应,“理想的”女性身体应该纤细:“身材、毛发和手要长,耳朵、脚、牙齿要短,指甲、嘴唇、面颊要红,腹部、嘴、肋部要细。”[35]越能从身体上衬托男性的强大,女人就越“美丽”。随着这个趋势的发展,一个性属-性别逐渐成为“小的代名词”。[36]为了凸显女性的“小”,西方曾流行紧身褡:
布拉邦特“非常贴身的”紧身上衣能使“上身显得优雅并且苗条”,西班牙女上装“两侧那么窄”,人们难以理解它如何能够容下身体。不管怎样,瘦身强调上装要“短”、“挺”、“紧”。……而唯一一种不束腰的特殊情况就是穿宽大的丧服时,这时外形可以忽略不计。[37]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为了争夺男人的目光,女性不得不追求柔弱美、纤小美、弯曲美。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产阶层女性履行着自身有关‘纤弱’女性的刻板印象”,“三天两头卧病不起”,“以各种方式表现出被动和服从”。[38]随着这种身体美学的兴起,高大、丰满、强壮的女性总是被排挤到低下的等级,“臂圆、脸红、穿着宽大的粗布衣服”的农妇几乎总是与美丽无缘。[39]
进入18世纪以后,西方审美文化的性别分野获得了理论上的表述。在发表于1757年的专著《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中,英国学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声称“美丽的事物都是较小的”:“我看到,在绝大多数论述中,令人喜爱的事物都被冠以小的称号。……我们很少说某物‘又大又漂亮’;但是,‘又大又丑’却很常见。” [40]与此相对,巨大的事物使人感觉恐怖,但可以激发人的崇高感。在性别层面,小/大对应着女(小女人)/男(大男子汉),因此,美更多地是女人的属性:“两种性别都无疑可以是美的”,“而女人则是最美的”。[41]“美是能够在人们心中激发起爱恋和类似激情的一种特质”,女人之美在于她“臣服于我们”。[42]这里的“我们”显然指男性。只有激发男性的爱恋之情,她们才可能被认为是美的。“换句话说,美丽只有在‘引起快感’时才存在。”[43]要唤起男人的爱恋之情,事物就不能过于巨大和强悍,否则,所产生的只能是恐怖感和敬慕之心。正因为如此,美总是意味着娇小、平滑、渐变、娇嫩、柔和:“要想使人体变得完美,要想使人体美发挥最大限度的影响,在相貌上必须具备温柔的、亲切的特征,而且应当在外观上保证柔软、光滑和娇嫩。”[44]对于喜欢征服的男人来说,这是一种引起愉悦的属性。他们愿意面对它,但不希望它出现在自己身上。对于男人来说,崇高是更匹配其性别特征的美学范畴:“凡是能够以某种方式激发我们的痛苦和危险观念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以某种令人恐惧的,或者那些与恐怖的事物相关的,又或者以类似恐怖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事物,都是崇高的来源;换言之,崇高来源于心灵所能感受到的最强烈情感。”[45]巨大的事物、阴森模糊的场景、黑暗、狂野的力量、困难、无限的空间、刺耳的声音都会唤起挑战的意志,可以锤炼人的身体和精神器官,象征男性扩张自己的意志。归根结底,崇高意味着自我的放大。它属于拥有权力的男性。女人只配拥有美:一种自我压抑、克制、驯服的属性。在身体层面,美与崇高对比鲜明:“一个体积非常大的事物或者一个身材非常魁梧的人不可能是雅致的,一个体积非常小的事物或者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不可能是威严的,而且只有那些能够进行某种运动的事物或者人才可能是优美的。”[46]事实上,具有优美特性的运动大多宁静、温和、柔顺:“女人的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虚弱和娇嫩,甚至是胆怯,后者是类似于娇嫩的一种品质”。[47]与优美不同,崇高则总是对应着挑战和斗争,显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从这个角度看,美/崇高的二分法明晰地敞开了性别层面的分野:
美 崇高
娇小 巨大
平滑 粗糙
柔和 坚韧
弯曲 直线[48]
在长篇论文《论优美感和崇高感》(1763)中,康德(Kant)延续了伯克的立场:“属于一切行为之优美的,首先在于它们表现得很轻松,看来不需要艰苦努力就可以完成;相反地,奋斗和克服困难则激起惊叹,因而属于崇高。”[49]“崇高就是那通过自己对感官利害的抵抗而直接令人喜欢的东西。”[50]“抵抗”需要力量,力量来自必须的男性身体,后者才能“以无畏的勇气面对工作和困苦”。作为“优美”的代表,女性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
第一个把女性构想为美丽的性别的女人,可能或许是想要说什么奉承的话,但是他却比自己所可能相信的更为中肯。因为就是不去考虑比起男性来,她那形象一般是更为美丽的,她那神情是更为温柔而甜蜜的,她那表现在友谊、欢愉、和亲善之中的风度也是更加意味深长的和更加动人的。[51]
在康德这里,内蕴于伯克思想中的二分法获得了清晰的展示:男性-崇高/女性-优美。崇高属于男人,男人则是“高贵的性别”:“另一方面,我们[男性]也可以提出高贵的性别这个名称,假如说并不需要有一种高贵的心灵方式来拒绝荣誉的话——倒不如说是授予而并不是接受这个名称——的话。”[52]女人中或许会涌现出杰出者,但那不过是特例,并不能使整个性属变得高贵。同样,男人中即使存在低贱的个体,也无损于整个性属的地位。高贵者的基本特征是高,恰如伟大者的最突出特征是大:
我们说一个孩子美,尽管他矮小,但是一个美男子必须是高个子;至于女人,我们对这种品质的要求就少一些,我们可以说一个矮小的女人美,而不能说一个矮小的男子美。这时我们似乎不仅仅观察物体本身,而其还联系到它们在大自然,在大的整体中所占的地位。[53]
在这里,“在大的整体中所占的地位”显然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所指——由于“自然”的安排,男人与女人位于不同的阶梯,具有高低贵贱之别。正因为如此,矮小的男人不可能美,比男人高大的女人则是反自然的产物。无论如何,男人高于女人这个事实意味着优越性。涉及等级关系时,“高贵的性别”与“美丽的性别”就会显现出本质性的差异:“崇高必定总是伟大的,而优美却可以是渺小的。崇高必定是纯朴的,而优美则可以是着意打扮和装饰的。”[54]二者对比鲜明,显现出高低、主次、贵贱之别。在庄严的场合,优美时常是一种衬托和补充,“使崇高感因之能起作用”。[55]就本质而言,优美是事物可以占有的属性——可爱。倘若这些事物拒绝被占有,这类属性就会消失。获得“优美”之誉的人应该强化这种属性,以便受到强势主体的认同。当这种属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优美就会进一步柔化,变成席勒(Schiller)眼中的秀美:“如果精神在依赖于他的感性自然中表现出,自然非常准确地传达他的意志和非常富有表情地表现他的感觉,并不未被感性对于作为现象的自然所提的要求,那么人们称为秀美的东西就产生了。”[56]“真正的秀美只让步和迎合,相反伪装的秀美却融化。”[57]秀美的女性被打量、承认、称赞:“那是一种均匀的体态、身裁合度、眼睛和面孔的颜色娴雅地相配合,是在花丛之中也会让人喜爱并会博得人们冷静称赞的那种美。”[58]
随着上述逻辑的敞开,审美的性别分野日益明晰:“对身体的审美最终给了女性:力量与美丽区别开来。”[59]“最初的现代美只是针对女性而言”,女性成了“美丽的性别”。[60]这似乎是女性的胜利,但实为女性的失败:虽然“美丽使女性提高了身价”,但美与崇高的区别意味着新的等级。与其说这是赞美,毋宁说它是贬抑。通过具有吊诡意味的词语转换,一种等级制的性别美学被延续下来:“女性仍然避免不了地位‘低下’,因为美丽是为了‘愉悦’男人或更好地为男人‘服务’而更加处于从属地位。她是为他创造的,只为他着想:她有可能升级,但那是在文学中,而不是社会中。”[61]正因为如此,“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声誉不佳。它被当作低下的属性,时常激发人的物质性的贪欲和占有之心。[62]由于其蛊惑性,“美”曾被政治学等与上层建筑相关的学科放逐:首先,通过占据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分心,美的事物可能令我们不再关注错误的社会安排;其次,当我们打量一个美的事物并使之成为持续关注的对象时,我们的行动对于它来说可能是破坏性的。[63]
三
到了20世纪,审美场域的性别分野依然延续下来,与之相应的二分法则继续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恰如布尔迪诺(Pierre Bourdieu)所言,人们仍旧根据某些基本模式来评价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身体,形成“从大/小和男/女的对立出发的一种反应”。[64]于是,有关男性精神与女性气质的言说依然弥散于公共场域和私人空间,影响着人们的思与行。
在20世纪乃至当下,性别层面上的审美评估还延续着伯克所阐释的逻辑:“她作为女孩太壮了”,“这对男孩来说算不了什么”,等等。(同上)作为占据优势地位的性属,男人仍以身体高大为美:“如果你结交了块头大的朋友,你会想变得和他们一样。尽管你可能没办法做到这点,但这个念头却会时刻萦绕于你的心头。”[65]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女性则继续以自己的柔弱之美衬托崇高的场域:“在富裕的西方社会,苗条(slenderness)与幸福、成功、年轻和社会吸引力相关。身体过重则意味着懒惰、缺乏力量意志、失控。对女人来说,理想的身体必须细瘦。”[66]当一个女人看到比自己娇小的同类时,她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羡慕之情:“我打量比我娇小的普通人。尽管我想‘她并非真的漂亮’,但打击我的第一件事却是‘她娇小’,而我愿意看上去像她。我一点也不认为她漂亮,而仅仅是想变得苗条。”[67]正因为如此,20世纪影响深远的美学名家贝尔(Clive Bell)曾说:“世界上最美丽的事物是美丽的女人,次一级美丽的事物是她们的画像。”[68]无论此说是否精确,崇高/优美二分法依旧延续下来却是个不争的事实。由于当代整容手术日趋发达,这套话语“遵照有关青春活力、女性特质(femininity)、男性特质(masculinity)的具体观念”,“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引导人们“重新构建自己的身体”。[69]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90年代,美国就有超过200万妇女试图通过隆胸手术而使自己更有“女人味儿”;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男人接受各种手术,以求看上去更显肌肉强健,花钱购买一副更显“完美男子气概”的身体。在这种语境中,诸如什么样的体形完美、标准面角、最佳服饰之类的话题似乎都有标准答案,定期由美学家、服装设计师、美容权威发布。符合此类条件者会成为大众文化的宠儿,其他人则要“同身体和无法合格的外形作斗争”。[70]
在反思这种分裂的身体美学时,部分东欧思想家将之归结为当代拜物教:随着大众传媒的崛起,女性身体获得了更多的展示机会,但却因此被客体化和商品化。[71]此种论点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由于世界正在迅速图景化,男性身体也同样被大量展示(男明星的受欢迎程度并不亚于女性艺人),为何却没有因此成为“美丽的性别”?诸如迈克尔·杰克逊、施瓦辛格、贝克汉姆之类明星常常意味着收视率,但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他们的创造性、强健、敏捷而非仅仅是外表的赏心悦目。的确,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充斥着有关专题,讨论身体意象/形象,整形手术,如何让身体看上去始终青春焕发、性感十足、美丽动人,有关减肥和健身的生意现在成了千万美元的大产业。”[72]不过,传媒之为传媒,在于它并非独立的权力主体。在其背后,更深层的权力体系在运转,决定着世道人心。对于波伏娃等人来说,两性的地位决定于他们所占的世界份额。二分法之所以长期流行,是因为“两性从来没有平分过世界。”[73]即使到了波伏娃写作《第二性》的20世纪50年代,下面的性别分野依然清晰可见:“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74]于是,男人的身体依旧通过自己获得意义,女人的身体则必须接受男性的审视、评估、取舍:“她像一幅画、一座雕像,像舞台上的演员,一个类似因素,暗示出一个不在场的主体……。”[75]与女性相关的绘画、雕像、演员都是看的对象:
女人在首饰、边饰、闪光片、假发的打扮下,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玩偶;甚至连这肉体也在展示;就像花朵无偿地盛开一样,女人袒露她的肩膀、背部、胸脯;除非在狂欢时,男人不应该表明自己在觊觎她;他只有权注视和跳舞时拥抱她;但是他可以沉醉于成为一个奇珍异宝的世界的国王。[76]
看的主体规定了被看者的自我塑造。这个主体就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他即便表面上缺席了,也依然是居高临下的塑造者。在他的注视下,女性只能按照主流尺度装扮自己:对于她们而言,“身体成为一项规划的方式与其说表达了她们的个体性,似乎更像是反映了男性的设计和幻想”,相应话语“鼓励女性按照男性的审美观来改变自己的身体”。[77]于是,通过凸显身体塑造的性别维度,人们延续了既存的社会不平等。因此,要超越审美的性别分野,就必须首先解构相关的二分法。
事实上,身体的性别分层绝非仅仅源于自然法则,更是一种人为建构:如果上/下对应着男/女,那么,人的社会性别必然是个变量,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单一的生理学因素。按照等级制的逻辑,同一性别的人中也有贵贱之分。面对主人,处于下位者应该表现出阴柔气质。在某些时刻,人的社会性别与自然性别恰好相反。事实上,当占据较高社会位置的女性向男人发号施令时,男性化的女人已经在统治女性化的男人。正因为如此,地位低下的男性也会放射出阴柔之美:“男人支配女人,不过,同时也有父亲对儿子的支配。由于阳性身份被视作性的力量、对女人的权力以及政治支配力,所以,未婚男性被逼进在许多方面与女性角色无异的依赖性社会角色。这样的社会定位所产生的后果是年轻男人有一种准阴性人格。”[78]对于少数掌握了权力的女性,人们常常不吝啬赞美之辞,仿佛她们是男人中的女人。事实上,阴性人格不是一种生理学的对应物,而是社会建构的产品:它属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为了展示自己的阴柔之美,古代的部分男性也曾缠足:“缠足的人的性别为男性、女性、中性,年龄在20岁之前。”[79]通过缠足之类活动,他们建构出自己的社会性别。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自我塑造:甘愿处于等级制阶梯的下层。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并非永远重合。恰如布尔迪厄(Bourdier)所指出的那样,男性气质曾长期被等同于贵族风范。[80]归根结底,它是一种阶级属性而非自然差别。处于上层的统治者才是永远的男人,女性是被统治者的隐喻。只有建立起真正平等的社会结构,等级制的身体美学才会被舍弃。
实际上,反向的运动早已出现,只是它尚被主流话语所遮蔽。文艺复兴时期,平等意识的出现就部分改变了上层社会的性别关系。在回顾这个变化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曾以自信的口气说:“要了解这一时期的高级形式的社交,我们必须先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妇女和男子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81]此说虽然失于片面(讽刺女性仍是当时的习俗),但却敞开了一个趋势:随着现代精神的播撒,女性也站在走向新世纪的门槛上。与此相应,部分意大利作家开始撰写《妇女的光荣》、《保卫妇女》、《拥护罗马妇女》等专著,力图塑造积极的女性形象。[82]在16世纪写作《愚人颂》(In Praiseof Folly)时,荷兰神学家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Erasmus)曾说:“我问你,神或者所有人是从哪里生下来的?从头部、脸上、胸膛、受或者耳朵?从所有这些被认为是体面的身体部位?不,不是这样。繁殖人类的器官真不像话,一说出口看引人发笑。这里有一道真正的圣泉,万物的起源皆由此出,而不是来自毕达哥拉斯的四元数。” [83]显然,这里所说的圣泉不但与女性相关,而且意味着对女性的肯定。这种肯定源于深层的社会学背景: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民主制度的生成,女性逐渐走向独立。这个过程进展缓慢,充满了复杂的博弈,但其箭头却始终指向前方。对此,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波伏娃等人曾经进行过认真的总结:在16世纪,部分上层社会的女性争取到了受教育权,并且开始部分涉足以前完全由男性占据的职业(如1545年女演员出现于公共舞台上);[84]到了17-18世纪,女性已经能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1880年以后,妇女被允许有自己的财产;1919年,妇女争取到选举权。[85]由于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女性开始大量参加生产劳动,“找到了经济基础”,其地位的上升甚至使男人感受到了威胁,以至于后者开始自觉地延宕上述进程。[86]不过,这种阻拦并未改变总的趋势。在19世纪后半叶,性属不再被当作不可挑战的尺度:“从1860年到1870年这段时期,法律、司法地位、医学科学和社会管理机器的变化开始迫使个体的性属变得模糊起来。”[87]进入20世纪,女性主义开始拆除阻碍身体走向自由的藩篱:
今天,女人比以前更加了解通过运动、体操、沐浴、按摩及健康的饮食来开发身体所带来的乐趣;她自己决定自己的体重、体型及肤色。当代的美学观念允许女性将美丽与活力结合在一起:她有进行肌体训练的权利,她拒绝发胖;在体育运动中,她把自己作为主体而自我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从她偶然的肉体中解放出来。[88]
于是,女性可以“有肌肉、灵活、健壮”,“像劳动者的身躯一样黛黑”。[89]与此相应,部分人开始拒斥理想化的身体意象。“理想化总是以进行理想化的自我为代价”,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自我-理想”使人与自我剥离,实现它的过程必然损伤人的个体性。[90]在性别领域,“理想化”的结局是绝对化:“通过把平均差异转换成绝对差异,才会产生出‘女性’和‘男性’这两种彼此分离、不相平等的范畴。”[91]譬如,“男人比女人更强壮”之类说法就忽略了一个事实:有许多女人比许多男性强壮。强壮和柔弱是男人和女人都可能有的特征,崇高/优美的二分法忽略了男女身体之间的共性。它夸大差异,将生物属性的意义转换成一系列新的对立。从20世纪开始,这种人为的分界不断被挑战和逾越:部分女性试图“过男人的生活,但保持女性的本色”。[92]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自由的差异性”,力图塑造多元化的性别形象:男人可以美丽,女人有权强壮。[93]随着这种自觉的身体塑造,传统的主体/客体分野也被逾越:女性不再仅仅是被观看的客体,更是自我观看和相互观看的主体。[94]随着这个趋势的发展,一种超越性的主体之美已经显现。它虽然微弱而模糊,但却注定拥有未来。不过,如何为新的身体美学进行定位却颇费周折:既要承认性别差异,又必须追求差异中的平等和平等中的差异,故而分寸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但由此产生的论争乃至龃龉又展示了问题的复杂性。显然,这是个拥有未来的课题。
简短的结语
在西方审美文化场域,消除性别层面的二分法至今仍然是一种进行中的工作。由此产生的解构性力量还不能与主流话语对抗。在日常生活、艺术创作和传播、意识形态中,后者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建构。中国目前流行的“女汉子”之类称呼就反映了同样的二元论思维模式。正因为如此,相应工作业已扩展为全球性实践。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加入到博弈的行列会使汉语美学直面世界性问题,获得重新出场的重要机缘。
[①]Donn Welton, The Body: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1999), p.36.
[②]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刘晖译,第30页。
[③] [加] 约翰·奥尼尔:《身体五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李康译,第33页。
[④]《男性统治》,第8页。
[⑤]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王晓朝译,第227页。
[⑥]Plato, The Republic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3), p.162.
[⑦] Aristotle, Poetics(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96), p.7.
[⑧]Aristotle, Rhetoric (New York: DoverPublications.Inc), 2004, p.19.
[⑨]Politics, p.21.
[⑩]Republic, p.169.
[11] [德]利奇德:《古希腊风化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杜之 常鸣译,第529页。
[12] Ariana Traill, Women and the Comic Plot in Menande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70.
[13]Women and the Comic Plot inMenander,p.246.
[14]《古希腊风化史》,第463页。
[15]Republic, p.194.
[16]《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第563-564页。
[17]《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第572-573页。
[18] Rhetoric, p.18.
[19]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苗力田译,第93页。
[20] Saint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0), p.840.
[21]The City of God,p.839.
[22]The City of God,p.842.
[23] Thomas Aquinas, BasicWritings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Volume One-II(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1997), p.480.
[24]Rex Warner trans. The 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1963), p.189.
[25][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何新译,第390页。
[26][英]弥尔顿:《失乐园》,(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金发燊译,第130页。
[27]Jonathan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London:Picador, 2000), p.177.
[28][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渠敬东曹卫东 译,2006,第216页。
[29][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何新译,第390页。
[30][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王义国等译,第510页。
[31] [德]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何兆武译,第31页。
[32] [法]波伏娃:《第二性》(I)(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郑克鲁译,第161页。
[33]波伏娃:《第二性》(I),第57页。
[34] [法]乔治·维加莱洛:《人体美丽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关虹译),第32-33页。
[35]《人体美丽史》,第43页。
[36]《人体美丽史》,第35页。
[37]《人体美丽史》,第55页。
[38] [英]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李康译,第107页。
[39]《人体美丽史》,第41页。
[40] [英]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郭飞译,第96页。
[41]《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第84页。
[42]《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第79页。
[43]《人体美丽史》,第95页。
[44]《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第100页。
[45]《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第36页。
[46] [英]安妮·谢泼德:《美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艾彦译,第92页。
[47]《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第99页。
[48]《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第106页。
[49] [德]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何兆武译,第30页。
[50]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邓晓芒译,第107页。
[51]《论优美感和崇高感》,第28页。
[52]《论优美感和崇高感》,第28页。
[53] [法]狄德罗:《狄德罗美学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张冠尧桂裕芳译,第33页。
[54]《论优美感和崇高感》,第4页。
[55]《论优美感和崇高感》,第5页。
[56][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上海:译林出版社,2012),张玉能译,第259页。
[57]《审美教育书简》,第283页。
[58]《论优美感和崇高感》,第39页。
[59]《人体美丽史》,第33页。
[60]《人体美丽史》,第29页。
[61][法]乔治·维加莱洛:《人体美丽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关虹译,第35页。
[62]ElaineScarry, On Beauty and Being Just(Pincetonand Oxford: Prince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7.
[63] On Beauty and Being Just, p. 58.
[64]《男性统治》,第87页。
[65] Gail Weiss, The Body Image: Embodiment and Inter-corporeality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1999), p.130.
[66] Body Image: Embodiment and Inter-corporeality, p.9.
[67] Body Image: Embodiment and Inter-corporeality, p.129.
[68] Clive Bell, Art (Charleston: Bibliobazaar, 2007), p.21.
[69]《身体与社会理论》,第6页。
[70][美]黛布拉·L·吉姆林《身体的塑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黄华等译,第13页。
[71]EllenE. Berry, Post-communism and the BodyPolitic (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2.
[72]《身体与社会理论》,第2页。
[73][法]波伏娃《第二性》(1),(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第14页。
[74]《第二性》(1),第9页。
[75]《第二性》(2),第365。
[76]《第二性》(2),第364。
[77]《身体与社会理论》,第8页。
[78]《身体与社会理论》,第191页。
[79] [日]冈本隆三:《缠足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马朝红译,第64页。
[80]《男性统治》,第82页。
[81][瑞士]雅克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何新译,第387页。
[8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87页脚注3。
[83] [荷兰]伊拉斯谟:《愚人颂》(上海:译林出版社,2010),许崇信译,第13页。
[84]《第二性》(1),第149页。
[85] [英]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史云龙等译,第593页。
[86]《第二性》(1),第17页。
[87]《身体与社会理论》,第79页。
[88][美]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程相占译,第130页。
[89]《第二性》,第353页。
[90] BodyImages: Embodiment and Inter-corporeality, p.30.
[91]《身体与社会理论》,第104页。
[92]《人体美丽史》,第195页。
[93]《人体美丽史》,第229页。
[94]《第二性》(2),第598页。